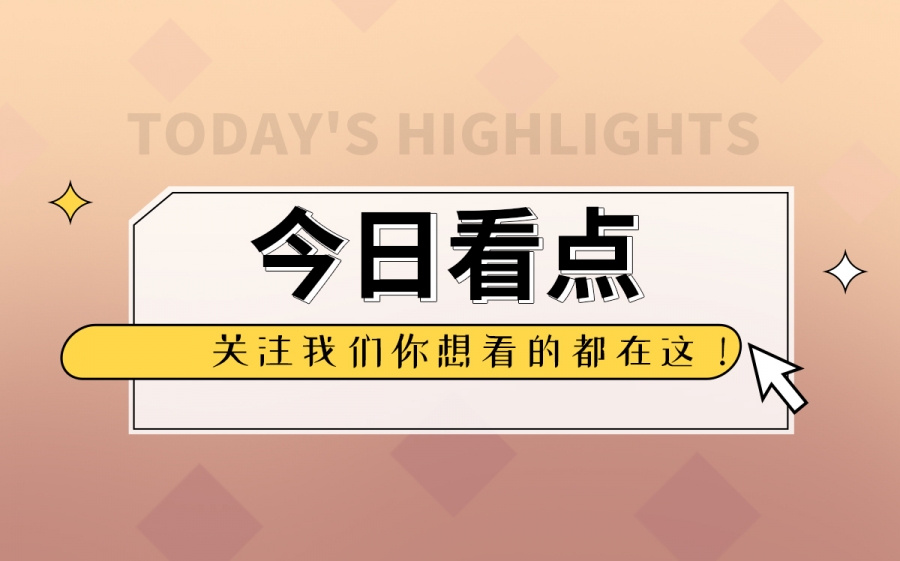让我们感谢花谷大师兄送来的助攻(鼓掌)(吹口哨)
“都是快要成家的人了,怎么还这么浮躁,嗯?”
方迟邑微低着头翻阅文书,不知怎的就走了神,捻住一缕垂落下来的头发想着是否该修剪一二,就见方殊辰随意地敲了几下门后推开一条缝钻了进来,可看样子又不像是有要紧事……八成是闲的。
 (资料图片)
(资料图片)
“什么啊……”一听到“成家”二字,方殊辰脑中迅速浮现出一个人的身影,这时候知道要不好意思了,伸出手佯作深沉地捂住了半张脸,凑上前来说,“咳,父亲如今一门心思都放在如何哄母亲上,我问什么他都讲没时间,叫我直接来找你,我便来了——”
方迟邑顺手将头发挽到耳后,发冠上的珍珠挂坠衬得他笑容明媚:“该不是想知道什么时候给你拟定婚事章程?”他又故意皱着眉笑骂一句,“一股脑想着要成亲啊,阿辰?婚姻大事怎么能操之过急!”
“不是……”方殊辰心虚地别开眼睛,说这话时吞吞吐吐的,“就……我不想让阿決多等,我知道的,他需要的不仅是一个答复!”
“你很勇敢……比很多人都要勇敢。”方迟邑一度以为自己是挤着笑的,可这声赞许却是脱口而出,“男子之间的相交难免惹来非议,不过兄长相信你,定会竭尽所有保护好那个人。”
方殊辰心头一暖,被感动得不行,扑他身上不说还险些抱上大腿:“迟邑哥哥……要是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你就直接吩咐,指哪打哪!断没有半个‘不’字!”
毛头小子一个。方迟邑颇显无奈地将人往边上推:“上赶着表决心啊……喏,就桌子上这些,你现在就帮我看了?”
“这、这个还是免了!”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字,方殊辰当即灰溜溜地爬起来,一张俊脸皱了起来,嘴更是撅得像能挂油壶,那叫一个嫌弃。
古往今来,不论高门还是寒居,有多少兄弟姊妹为了权力争得头破血流、手足相残?到了自己这,身边就一个闲散惯了不爱管事的傻弟弟,还一门心思都在“讨老婆”上——但方迟邑知道,这人绝不是窝囊。
“迟邑哥哥,你在想什么呢?”察觉到这人近不可闻的叹息,方殊辰还当是自己说错了什么话惹他不高兴了,正想着讲些好听的,视线却不自觉地落在桌上的一个墨黑色的椭圆形物体上。
在东西……像是块药玉?但那种材质不好保养吧……
方殊辰不敢细看,出于好奇就打算问了,可才拿手一指,对方极尽反常地将那东西拢进袖子收了起来,一本正经地拉开话题:“你今日课业可完成了?”
他顿觉不妙,就怕这人给自己额外安排工作,干笑两声就逃到了门边:“啊忘了忘了!我突然想起有一窝海獭崽还没喂,就先不打搅了——”
方迟邑顺手燃了香盏,撇下外袍丢在了一边,略显疲惫地捏捏眉心:“出去时把门带上吧,我想小憩片刻,莫要人来打搅。”
“哦好,迟邑哥哥莫累着了,好好休息!”
所谓的“休息”只是想要得到安静的借口。方迟邑将双手叠放在腹部,躺在床上盯着房梁看了一会儿直到眼睛发酸仍没有睡意,索性闭起眼;而藏在袖子里的东西正硌着他的侧腰,太具存在感——冰凉的,坚硬的,一如那人离去时冷落而决绝的目光。
他常在四下无人时尝图将这陶埙吹响,约莫是因为总摸索不到合适的姿势和口型,手指也不够灵活,总是把脸颊都弄疼了还找不准感觉。
方迟邑几乎认定这是天意,那些算不得全是爱情的心意,终究是得无疾而终——萧彻明曾同他言“有缘自会再见”,倘若这“缘”本就薄弱不堪呢?若他等不到那未来的某一天了呢?
回想起元轩枝之前的话来,他竟会不可控地嫉恨起方殊辰来——
那人不过是一个父亲顺手捡回来的孩子,明明这十余年来与自己共享蓬莱少主的头衔和地位了,为什么还能不必受到诸多约束,过得这么自在!
甚至敢狂妄到当他的面催着要娶一个男妻过门!
他的掌心被自己的指甲攥出红印,神识在这一刻短暂回笼:“阿辰,对不起了……”
……
新门主的继位大典安排在下月初三,据说是个不错的日子,蓬莱上上下下忙碌而热闹;方迟邑不想大肆操办,但还是遵照礼仪派人给交好的东海世家们送去了宴请的帖子,说要的就是一个“同乐”。
依照元夫人的嘱托,温鸿一每日会给方迟邑送去安神益补的汤药,无意间听人说起大公子桌上放着不少女子画像的事,当即眉头一皱:
他跟那个衍天宗宗主的事黄了?
“你也知道我身子不好,这些是给阿辰准备的。”方迟邑一手撑着下颚,毫笔在纸上浅浅画过,同时微微笑着,“老大不小了还没个正形整天想着乱跑,我不过说了他两句,竟出言不逊肆加顶撞!过年就及冠了,总还想着玩可不行啊,或许成了家能收敛些……现下父亲母亲外出游玩,我身为阿辰的兄长,擅作主张一回也无可厚非。”
“大公子,你不觉得——”温鸿一还想隐晦地“提醒”一二,就觉这人正以余光看着自己,他的唇角分明是上扬的,可是语气半分不带笑意:“温小宗主,你今天的药也送到了,可还有事?”
温鸿一轻声叹息:“我打算去看看小公子,送点润喉的汤品啥的,你不怜惜他我怜惜他!被禁足后他闹了好阵子,饭食不肯动,那嗓子怕是要废了……”
“随你吧。”方迟邑也不是想将事情做绝,经他这么一讲自然是动了恻隐之心,但还是补充,“你最好是真想帮他,而不是纵容。”
其实这几日来方迟邑也不止一次去方殊辰那规劝,可那人犹如吞了秤砣,说什么也不肯听,最后甚至连敷衍他的搭话也没有了。
“阿辰,你从前可是很乖巧懂事的。”夜深时,他将看守的侍从遣散,自己背靠在门扇上坐着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来,想到高兴的事情时便灌一口酒,待好几个酒壶见底,他百感交集道,“大人的世界有太多不可说和不得已了,可惜这些父亲没教过你,我也不期盼着你能很快就懂,不过等你……”
这人喝了很多,醉后格外坦诚。方殊辰并没有睡,最后也听见这人低低的啜泣声,和强撑着站起来踉踉跄跄离去的步伐。
继位大典那天,新门主因宿醉迟到了些,恰是在此空隙,方殊辰同温鸿一里应外合,竟用火药逃出了蓬莱。
方迟邑像是早料到有那么一出,也不遣人去追,而是不紧不慢地继续宴会的进行,他手一抬,负责歌舞表演的弟子环抱琵琶,衣袂翩跹,鼓乐不断。
元宜念抚摸他的脸颊:“你近日憔悴了许多,没在好好服药么?”这人做事一向周到,也正因为他这事无巨细的风格,不知花了多少心思在处理蓬莱事宜上才将一切都打理得一丝不紊……身为母亲,她的眉眼间皆是疼惜,“邑儿,你是不是在生阿辰的气?这孩子今日是做得过了些,还有鸿一,两个人怎么能一起乱来!”
他将自己的手搭在元宜念手上,柔声安慰道:“母亲,阿辰再怎么说也是我弟弟,我这点气量还是有的,你莫忧虑太多,过阵子我就将人接回来……”
方迟邑带着几个高阶弟子亲临万花谷的那日,方殊辰将所爱之人护在身后,眼神中皆是戒备,不是完完全全的冷漠,却足以让彼此都觉得对方陌生。
此时的他就像一把独具锋芒的刀刃,无论是谁想要靠近,都会被斩得破碎。
“阿辰,该回去了。”
方迟邑向他招了招手,同时面带微笑地向一袭黑衣的万花弟子点头示意——这人的相貌本就不出众,又因为大病初愈,头发半散着,整个人摇摇欲坠,一张脸更是泛着可怕的白。
这样的人如何配得上自己的弟弟呢?方迟邑略显悲观地想:还是说真的要提些更过分的要求才可以吗?
于是“孩子”一事再被搬到了台面上讲。
要男子生孩子,这是何等屈辱之事!
“方迟邑!你要闹哪样!你多爱那个姓萧的啊,有本事你先给他生一个啊!你为难阿決算怎么回事!他是我的!我这辈子就认定他一个人了!”方殊辰忍无可忍,险些就要冲上去狠狠揍一顿自己这个混账哥哥,但是很快遭到了随从们的控制,乱吼的嘴也被软布勒住。
“阿辰……最好注意你现在的身份,怎么都不会跟哥哥好好说话了?”
而就在众人暗暗唏嘘、讶异之时,那万花弟子表现得格外从容,丝毫没有被对方的气势压制,反倒淡淡吐出几字:“仅此而已?”
方迟邑无不欣赏地重新打量他:“仅此而已。”
自己只是想要这两个人都知难而退罢了——他在心底反复呢喃。
……
各家各派多的是护短的主,方迟邑料到自己在万花谷“惹是生非”定会受到报复,可还是被一只红栗色的松鼠引入深林遭了黑手,被“百花拂穴手”封去内力的他压根没有力气挣脱束缚。
“我现在仔细看了,方门主也算得上是一个美人儿了,可惜生了副坏心肠……”对方的长剑并没有伤人的意思,却是轻轻将方迟邑领口玉石扣挑开,露出软缎下雪白的脖颈,胸口大片肌肤更因急促呼吸而起伏着,仿若任人采撷。
“某虽不才,但也有些门路……这宫廷秘方乃滋补圣药,按说不该流入民间,可如今与方门主投缘,自当相赠——”
药液被悉数强灌入口,缀着珍珠银饰的系腰丝绦随即滑落,冰冷的金属剑鞘轻而缓慢还在游走,确保不会留下太过显眼的伤痕;方迟邑本咬着牙不愿发出耻辱的声音,可粗糙的触感令他不爽至极,那星星点点崩溃的情绪正在将理智研磨殆尽,慢慢化作自己听不懂的告饶哀求。
“这便是辱我门中弟子的后果,方门主,你好好受着罢……”
“那个不……至少别、别用那个唔——”
对方从方迟邑怀中搜出那缀着红穗的漆黑的陶埙,发出一声微不可察的哼笑,找了一个更适合它的位置推塞了进去。
撕裂般的痛楚刺激着方迟邑疼得浑身发颤,疑心那该是多可怕的一个创口,哀哀低吟:“我一定会杀了你!你枉为医者——”
“起来了……”对方饶有兴致地笑着离去,似乎还在同他挥手作别,“多谢方门主为我提供了治疗痿症的思路,值得一观。”
然而方迟邑早已没了骂人的力气,连喘息都显得格外吃力;恍惚间,他感受到剧烈的耳鸣,疲惫感由内而外想要吞噬一切,让他觉得自己真要以如此不堪的褴褛姿态死去。
“嘤嘤嘤……嗷嗷……”
那是绥绥的叫声。可是方迟邑的害怕深入骨髓,哪怕那一片火红皮毛映入眼帘他也还是认定这是幻觉。
直至身前的男人撩开他被汗濡湿的头发,柔声说了一句:“怎么弄成这样?”
方迟邑说不出话来,不再去思考萧彻明为何会出现在这里,被人解救后腿脚发软也跑不掉,竟选择欺身而上主动纠缠,整个人的色气都是红润润的。
“这一次,不许拒绝……”